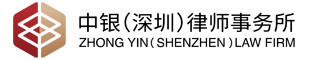案件背景
據網絡新聞報道,2023年1月,男方席某某和女方吳某某經婚介所介紹認識。2023年5月2日訂婚擺宴席后,兩人在婚房發生關系,女方控訴男方強奸,事件引發熱議。
同年12月25日,一審法院查明,在房內男方不顧女方被害人反對,強行與被害人發生了性關系。一審認定被告人違背被害人意志,構成強奸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男方當庭上訴。席某某及其家屬堅稱席某某無罪,席某某母親還表示,雙方是自愿發生性行為,女方是就房產本上需加名一事和男方發生沖突后開始抱怨。
2025年3月25日,該案二審在大同中院庭審結束,將于2025年4月16日宣判。
案件分析
根據網絡上的報道,筆者認為,本案認定男方席某某構成強奸罪的定案證據為被害人供述及被害人母親與被告人的對話錄音。
首先,據被害人陳述,早在兩人交往之初,女方就跟男方說過,自己不接受婚前性行為,并且是堅決抗拒,而那天在婚房里,男方強行要與她發生性關系,為了反抗,女方試圖逃出房間喊“救命”,卻被男方強行拖拽回了案發現場,女方還點火燒臥室的窗簾和柜子企圖自救。最后女方左右大臂和右手腕處,均有淤青,手機也強行被男方拿走。
其次,男方席某某與女方母親之間存在一段錄音。錄音中,女方母親詢問“你們訂婚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吧”,席某某予以肯定回復;女方母親追問,“你對吳某某進行強暴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吧”,席某某回復“哦哦”。
筆者認為,以上兩證據為本案定案的關鍵證據所在,一審法院的裁判觀點大致應為被害人的供述與案發現場情況、傷情情況能夠相互印證,男方也在事后對其強奸行為進行了自認,足以證明構成強奸罪。
然而,本案之所以引起社會廣泛討論,重要原因在于社會公眾對男方與女方訂婚后能否構成強奸罪存在爭議及二審階段出現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相反證據,如醫院診療手冊和鑒定書里記錄的“處女膜完整”“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針對司法實踐中對于強奸罪存在的爭議及本案的疑點,筆者具體分析意見如下:
一、訂婚期間或婚內強奸,是否構成強奸罪?
我國《刑法》第236條明確規定,強奸罪是指違背婦女的意志,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系的行為。然而司法實踐中,對于婚內強奸是否構成強奸罪長期存在爭議。
該行為的主要爭議點在于,婚內強奸是否成立“違背婦女意志”這一要件。支持婚內強奸構成犯罪的觀點在于,性同意完全獨立于婚姻關系,法律明確規定了只要違背婦女意志,即構成強奸罪,與雙方身份無關;不支持婚內強奸構成犯罪的觀點在于,婚姻契約中默認包含性義務,妻子同意結婚即構成對夫妻生活的“概括性承諾”。
現階段普遍的觀點及裁判案例均認為,婚姻存續期間,即使丈夫使用暴力、脅迫手段與妻子發生性關系,通常不認定為強奸罪。原因就是妻子在結婚時作出的“概括性承諾”。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形,若婚姻處于非正常狀態(如分居、離婚訴訟中),視為“婚姻關系空殼化”,此時性自主權受保護(如浙江省安吉縣“離婚訴訟期間強奸案”、河南省三門峽“分居期間強奸案”),暴力強迫性行為可能被認定為強奸罪,但量刑可能從輕。
我國《民法典》第1049條明確,婚姻效力以登記為準。然而在本案中,男女雙方僅舉辦了訂婚儀式,未辦理結婚登記,訂婚僅為民間習俗,無法律約束力,雙方仍為未婚狀態,故性行為的合法性完全取決于女方是否同意。若女方明確拒絕,男方強行發生性關系即構成強奸。
綜上,本案中只要能夠證明男方席某某在女方明確拒絕發生性行為時仍然采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強行與女方發生性關系,即構成強奸罪,與雙方已經訂婚的狀態無關。男方母親提出的“女方經常到兒子婚房休息,并會發生一些親昵的舉動和行為,家里還有女方的貼身衣物”等抗辯理由,不影響案件的定性。
二、司法實踐中認定構成強奸罪需要什么證據?
首先,筆者結合自身辦案經驗和司法實踐情況認為,鑒于強奸罪犯罪證據采集難度較大,公安機關對于強奸罪的立案標準相較于其他犯罪較低。在強奸罪案件中,只要報案人能夠完整指認犯罪事實并明確指認犯罪嫌疑人,無需提供進一步的物證或傷情鑒定,即可啟動刑事立案程序。
其次,在證據采信方面,相較于其他犯罪,辦案機關對于被害人陳述的信任度更高,犯罪嫌疑人想要脫罪需要提供更有力的證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強奸罪犯罪過程私密性極高,若事后并未積極保存證據,可能導致強奸罪中只存在言詞證據。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必然會作出無罪供述,那么案件就無從查證。另一方面,女性在強奸罪中處于絕對弱勢地位,作為強奸罪的被害人不僅身體健康會收到影響,名譽權也存在受損可能,提出強奸罪的指控本身對其就是一項挑戰,現實中出現誣告陷害的可能性較低。
但是,根據我國法律規定,要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不能僅憑借被害人的陳述,只有有其他證據能夠與被害人陳述相互印證時,才能對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判決。
具體到本案中,能夠與被害人陳述相互印證的證據有被害人的傷情鑒定及男方席某某與被害人母親的對話錄音。錄音中席某某對“你對吳某某進行強暴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吧”問題的肯定性回復,在刑法上構成對犯罪行為的自認,能夠與被害人陳述相互印證,足以認定席某某構成強奸罪。然而,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自認并非無法推翻,若席某某在二審階段能夠有力的指出該錄音真實性、合法性存疑,將該錄音作為非法證據排除,或者能夠自圓其說作出合理解釋,也存在翻案可能。
三、本案中的“處女膜完整”“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證據是否可以推翻一審判決?
上訴書披露,2023年5月6日,女方在警方的帶領下到大同市第一人民醫院進行檢查,醫院診療手冊顯示“處女膜完整,未見新鮮破口”。5月19日,大同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書部分內容顯示“送檢的女方內褲、陰道擦拭物、衛生紙上可疑斑跡中均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以上證據看似對被告人席某某十分有利,但是在強奸罪的認定中,處女膜是否破裂,是否射精,并不是構成強奸罪的唯一標準。
首先,我國法律規定,對于成年婦女的強奸罪,既遂的標準是行為人是否成功將生殖器插入被害婦女的體內。處女膜完整,不能代表沒有強奸行為。在醫學上,處女膜是否完整與是否發生了性行為不存在必然關系,不能以該證據作為認定不構成犯罪的依據。同樣,如果女方的處女膜破裂,也不能以此證明男方實施了強奸行為。
其次,即使“處女膜完整”“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的證據能夠證明被告人席某某不存在將其生殖器插入被害婦女體內的行為,也無法排除存在強奸罪未遂的可能,仍然構成強奸罪。
再次,作出診療手冊的醫院可能并非公安機關指定的鑒定機構,該證據不屬于法定的刑事證據種類之一,故“處女膜完整”的證據不一定會被二審法院所采納。
綜上,席某某上訴書中提到的“處女膜完整”“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證據并不能證明其不構成強奸罪,若能提出更多新的證據與之相互印證,才有推翻一審判決的可能。
四、男女雙方先談判后報警是否影響案件定性?
強奸罪的認定關鍵在于行為時的主觀意圖及客觀行為,而非事后態度。若席某某確實實施了強奸行為,實施完后犯罪已屬于既遂的終局形態,不可挽回,即使女方最初為了與男方談判未立即報警,只要證據證明性行為發生時存在“違背婦女意志”的情形,仍可定罪。
五、被告人家屬控告辦案人員涉嫌玩忽職守罪能否成立?
據悉,男方席某某母親前往大同市檢察院提交控訴材料,請求追責12名辦案人員玩忽職守罪。《控告書》披露,相關單位在辦理席某某涉嫌強奸案件中,存在“警方未等待DNA鑒定意見,即向縣檢察院錯誤報批”“檢方未等待DNA鑒定意見,作出錯誤批捕決定”“警方申報批捕所附卷宗50頁,統計案卷實際有69頁,至少少報19頁”“警方移送審查起訴所附卷宗150頁,統計案卷實有99頁,至少漏報51頁”“一審辯護律師2023年11月28日提交《撤回起訴申請書、羈押必要性審查申請書及公開聽證審查請求書》均未給予任何回復”等內容,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不正確履行職責,致使目前案件造成嚴重惡劣社會影響,對此該兩單位所涉及的主要負責人及直接責任人員應當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條玩忽職守罪。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報批捕、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的條件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但并未對具體證據的種類作要求。對于強奸罪來說,公安機關一般是在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后,才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但等待DNA鑒定結果時間較長,普通強奸案件中公安機關刑事拘留的期限最多只有7日,加上檢察機關審查逮捕的7日,最長辦案期限不過14日,往往等不到鑒定結果辦案期限已屆滿,故檢察機關只能根據現有證據進行判斷,如果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就會做出批準逮捕的決定。具體到本案中,是否“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并不完全依賴于DNA鑒定結果,若其他證據能夠讓犯罪事實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檢察機關批準逮捕席某某也并無不當。
對于席某某家屬提出的公安機關少報、漏報案件材料一事,該情節并非必然構成玩忽職守罪。首先,若辦案機關對少報、漏報的情況能夠作出合理解釋,實踐中也不會對相關人員進行追責;其次,從玩忽職守罪的構成要件出發,家屬需能夠指出少報、漏報的案件材料系能夠證明席某某有罪、無罪、罪重、罪輕的關鍵證據材料,對本案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影響,辦案人員的不當履職行為產生了嚴重的危害后果,才符合成立玩忽職守罪的條件。
綜上,筆者認為,僅憑現階段披露出的證據和文書來看,席某某家屬對辦案人員涉嫌玩忽職守罪的控告成立的可能性較低,即使本案中確有可能出現辦案人員存在工作失誤或疏忽,也未達到構成刑事犯罪的標準。
律師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