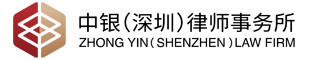一、案情簡介
周某于2021年6月7日入職A公司,該司將周某真實工資拆分成多筆發放至其多個不同賬戶。2022年11月2日,該司臨時通知周某等員工開會,周某等人到會并在簽到表進行了簽字,會上A公司表示相關部門將進行薪酬考核制度調整。2022年12月15日,周某領取到2022年11月工資,發現基本工資從原4500元/月降低為2880元/月。
2022年12月16日,周某申請勞動仲裁,索要被克扣的2022年11月工資差額。2023年2月22日,周某當日正常工作結束后,以公司存在隨意克扣工資、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等違法行為為由,向公司寄送了被迫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公司于次日簽收。勞動仲裁階段舉證期限內,周某相應增加、變更被迫解除經濟補償、年終獎、2022年12月至離職前被克扣工資差額等請求。
勞動仲裁裁決支持了周某前述請求,A公司不服裁決結果,起訴至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一審法院維持勞動仲裁裁決結果。
主要爭議焦點:1.工資結構與標準;2.在查明及認定該事實的基礎上,核心爭議焦點為:A公司規章制度雖然經過公示、告知以及所謂民主程序,是否可作為單方降低周某工資標準的有效依據,特別是存在職工代表比例不足等問題時,是否達到了民主程序的有效性標準。
二、代理意見
就主要焦點一:通過將周某所有賬戶款項流水、社保、公積金、個稅扣繳數據、代走賬數據及相應稅費補貼等一一梳理,同時比對與其涉及金額及薪酬對賬往來溝通的3-4名公司人事/財務/行政人員的微信聊天記錄,可證明周某主張的工資結構與標準屬實。A公司主張與客觀證據不一致、自相矛盾,不應采信。
周某的工資結構為:基本工資(2022年7月漲薪到4500, 2022年11月起被單方降為2880元)+績效(計件+浮動,根據公司績效方案核算)+各類津貼/補貼/獎勵(不固定),年終獎等。
A公司為達到避稅、模糊工資結構、利用員工賬戶代走賬等目的,將周某等人真實工資拆分成多筆發放,打到其多個不同賬戶。通過降低名義工資金額、制作不真實的工資條以所謂“工資”名義發放到一個賬戶(建行賬戶,賬號xx);剩余差額工資,則以所謂“報銷人員獎勵”“報銷績效獎金”“報銷獎勵金”“報銷競賽獎金”等名義,發放至另一個賬戶(光大賬戶,賬號xx或者通過私人賬戶補足)。A公司未發放完整真實工資條,發放金額中還存在代走賬款項。對賬時,A公司會將不同的金額/項目分批次拆散后交由公司3-4名行政/財務人員與周某進行分別對賬。
就此,承辦人通過一一梳理,剔除代走賬款項,比對與其涉及金額及薪酬對賬往來溝通的人員的微信聊天記錄,逐月復盤了周某每月真實的工資結構及標準情況,形成了工資梳理匯總表及其證據鏈條。
A公司主張周某的工資結構與標準為基本工資2880元/月+月浮動績效的說法,與客觀證據不匹配,加之其在工資標準變動時間點上出現了自相矛盾的陳述,在其主張與客觀證據不一致的情況下,應采信我方通過證據鏈條復盤的工資標準數據。
就主要焦點二:A公司系單方降薪,其薪酬考核方案等規章制度未依法履行《勞動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的民主程序,存在程序倒置情況,涉嫌事后違法補制材料。同時職工代表比例不足,職工代表中沒有周某所在部門推舉的代表,代表在代表性、廣泛性上均存在明顯問題,相關決議表決過程也存在出席代表人數不足等問題,不符合有關法規政策對職工代表及民主程序流程的要求,其薪酬考核方案不能作為對員工實施降薪的有效依據;A公司未與周某達成協商一致意見,其單方大幅度降薪行為無法律依據支持,不具有合理性。應駁回A公司訴請,維持仲裁裁決認定。
其一,關于民主程序倒置,涉嫌違法補制材料問題。第一,A公司的《銷售人員薪酬考核方案》,并非周某等員工(周某2021年6月7日)入職時的版本,A公司也未證明系周某入職時簽收過的版本,其上內容顯然與周某2022年10月以前的工資情況相左;第二,2022年11月2日,A公司臨時通知周某等在內員工開會,單方通知降薪,周某出席會議簽到不代表認可了A公司單方降薪的決定,更不代表A公司的規章制度合法,以及可以單方直接對周某實施降薪;第三,涉及降薪的考核方案第五頁第七條規定“本方案從2022年第二季度開始執行”,可推知其制訂形成的時間應在2022年3月31日前,相應召開職工代表大會、聽取企業工會意見的時間也應在2022年3月31日以前完成,但A公司提交的《第三屆職工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決議》,會議召開時間卻是在2022年10月31日,前后時間不符;表決文件與周某提交的文件名稱不一致。第四,A公司提供與案外第三人簽署的文件、郵件往來、單方制作文件等,試圖混淆爭議本身以及誤導事實的查明(如:《2022年11月21日電子郵件截圖及附件》,非屬于與周某往來郵件,三性不確認)。以上,足以證明A公司未依法履行與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討論、平等協商的民主程序要求,不具有合法性。
其二,《中國工會章程》、《職工代表大會操作指引》等對就職工代表人數比例、代表的廣泛性、代表性、選區分配名額等均有相關指引和規定,A公司民主程序存在職工代表比例不足、不具有廣泛性,不能代表全體職工的問題。第一,職工代表中沒有周某所在部門推舉的代表,代表在代表性、廣泛性上均存在明顯問題;第二,相關決議表決過程中職工代表比例不足5%,存在代表人數不足等問題,不符合有關法規政策對職工代表及民主程序流程的要求,該薪酬考核方案不能作為對員工實施薪酬調整的有效制度依據。
其三,即便不考慮A公司規章制度的民主程序問題,亦不能簡單以公司向員工進行了公示告知就認為該制度具有適用于員工的直接效力,規章制度的合法性內涵中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公司如果為達到單方降薪目的,只是進行簡單表面形式的民主程序,便試圖直接以單方修改后的規章制度來替代雙方原基于合意已簽署的個體勞動合同中對工資標準等重要條款的約定,不符合現行法律就變更勞動合同的基本要求,存在合法性問題,特別是在未達成合意的情況下直接以薪酬改革為由變相單方大幅度降低固定基本工資時應嚴格審查合法性、合理性。依據《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五條規定,A公司無證據證明就單方大幅度降薪與員工進行了充分的協商,并取得周某同意,不具有合法性及合理性,應予糾正。
三、裁決結果/案件結果
2023年5月18日,深圳市羅湖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仲裁裁決,全盤采信我方主張的工資標準、A公司民主程序不具有合法性等主張,裁令A公司:1.支付周某2022年11月-2023年1月克扣工資4860元;2.支付周某2023.2.1-2.22的工資差額890.34元;3.支付周某2022年終獎9000元;4.支付被迫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9828.22元;5. 開具離職證明。
仲裁裁決后,周某接受仲裁裁決結果, A公司不服裁決,起訴至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
2023年10月20日,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少見的詳細論證了A公司的民主程序未達到民主程序的有效性要求,指出A公司根據薪酬考核方案的內容,周某的月工資標準中的基本工資部分從4500元/月降低到了2880元/月,降幅接近50%,該大幅度降薪極大影響了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公司作為用人單位如主張按照《勞動合同法》第四條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民主程序單方大幅度降低勞動報酬,那么對職工代表大會民主程序的要求應更為嚴格,應當要求能夠代表大多數職工的真實意思表示,并有相關渠道允許勞動者提出異議及申訴,而A公司提交的民主程序相關證據沒有對待審議的薪酬考核方案開展前期征求職工意見的流程,僅在職工代表大會決議上載有11名職工代表的簽名,無法體現11名職工代表是否能夠代表該薪酬考核方案涉及的降薪勞動者的意思表示,而周某在2022年12月收到11月工資后即刻申請了勞動仲裁的行為已明確表示不認可前述考核方案。特別論述,A公司架構包括21個部門/機構,職工人數多達232人,但實際選舉出職工代表人數僅11人,職工代表人數比例不足5%,職工代表所在部門/機構僅8個且不涵蓋周某所在的部門,因此,不足以代表全體職工行使單方大幅度降低勞動報酬的規章制度修改的民主管理權,對相關薪酬考核方案不予采信,對公司主張的工資標準不予支持,采信周某主張的工資標準。據此,駁回A公司訴請,維持仲裁裁決結果。
一審判決后,A公司未上訴并按期履行了生效文書確定的法律義務。
四、案例評析
本案首先需要復盤周某真實工資標準,否則無法證明基本工資存在實際被降低,其他問題均無討論意義。如前所述,本案的工資情況查明及認定存在較大困難。經反復比對近一周時間,方完成復盤工作。
在明確工資標準后,核心問題是尋找民主程序漏洞。A公司的民主程序材料乍看非常完整,承辦人便按以下步驟抽絲剝繭:第一,查時間、地點、人物線,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形成、征求意見、表決通過、公示執行等民主過程時間點,相應由誰、于何時、在什么地點、以什么方式、由哪些人、做出哪些文件,又由誰、以什么形式、于何時、通知了哪些人,逐一審查;第二,比對現行法律法規政策,結合裁判實踐情況,從中找出不符合法律法規政策、邏輯和常理之處。
既往裁判實踐中,通常用人單位在形式要件上履行了民主程序要求,規章制度對勞動者進行了公示告知,如規章制度內容不存在明顯違法性或嚴重不合理的情況,裁判機關不會過度關注和審查參與表決規章制度修改流程所推舉的職工代表是否足夠具有代表性、廣泛性、是否足以代表全體員工進行民主表決這個問題。本案法官充分采信了我方主張,并以此作為否定單位規章制度的有效性的事由,對規章制度民主程序的規范性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和警示。
五、結語和建議
本案對職工代表的代表性及其規章制度民主程序流程的有效性的審查深度、廣度,較之既往同類案例,實屬少見。承辦人注意到,凡是涉及以修改規章制度為手段大幅度降薪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司法機關對規章制度民主程序審查力度往往更為嚴格。
正因此,借本案為例,做一分享,為同行在處理此類案件中提供參考方向,在參與指導企業完善規范民主流程時,應更加注意有關職工代表人數、比例、工會成員等民主程序參與者及規章制度修改、表決、公示等民主程序流程,是否遵循了《勞動合同法》《工會法》《中國工會章程》《職工代表大會操作指引》等法規政策文件的要求,盡可能避免民主程序流于表面形式,導致出現因明顯違反法規政策要求致使無法作為裁判及管理依據的不利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