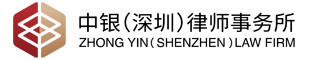01
概述集資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行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則是指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規、實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從而構成犯罪的行為。目前我國現行《刑法》對二者的法律規定為:
【集資詐騙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由于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二者均屬于非法集資類刑事犯罪,其在構成要件、保護法益、犯罪行為等方面均存在一些相似性,在司法實踐中也由于不同案件具體的犯罪情節、手段等的不同容易造成罪名認定的困難,或者在具體案件中出現對二者罪名認定的混淆和爭議等情形,而由于刑法對該二者的量刑幅度規定的不同,以何種罪名進行定罪處罰往往對犯罪嫌疑人的權益影響較大,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有必要對該二者從構成要件、保護法益、信任基礎等三個方面進行明確區分。02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區別(一)構成要件不同
根據刑法的明確規定,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構成要件上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主觀故意、客觀行為、非法集資款的屬性等方面。
首先,在主觀故意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關鍵。集資詐騙罪是行為人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意圖永久非法占有社會不特定公眾的資金,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行為人只是臨時占用投資人的資金,行為人承諾而且也意圖還本付息。
在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時不能僅從結果出發進行簡單的認定,即僅僅以行為人最終無法償還款項為由即認定其在向相關主體募集資金當時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應當從行為人募集資金時或者過程中,圍繞融資項目的真實性、資金去向的明確性、是否存在個人占有及揮霍等事實、證據進行綜合判斷。
非法集資類刑事案件的犯罪行為人往往會以某個投資項目的名義吸引或者引誘投資者進行投資,投資本身具有風險,投資者進行投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從中獲得收益,但這種收益是不確定的。如果因為項目本身出現虧損而無法償還投資者的相關投資款項,也是投資本身的特性所可能帶來的后果之一,不屬于刑事法律規范進行規制的范疇。刑法所規制的是那些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構投資項目等詐騙方法或者公然違反國家金融管理制度進行非法集資的行為。
目前學界關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有多種學說觀點,筆者認為采取“排除意思+利用意思說”能夠較為全面地詮釋“非法占有目的”的規范內涵,即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希望能夠排除權利人對財物的占有,并且利用該財物進行獲利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非法占有目的”采取了“列舉式+概括式”的規定模式,該司法解釋第七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實施本解釋第二條規定所列行為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的規定,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二)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
(三)攜帶集資款逃匿的;
(四)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
(五)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的;
(六)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的;
(七)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
(八)其他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其中,第一到第七款規定是對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觀行為的列舉,第八款規定則是對此的一個兜底條款。“非法占有目的”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一個主觀方面的要件,無法直觀地予以判斷和認定,需要根據行為人的客觀行為予以綜合判斷。從上述規定可以得知,司法機關是根據行為人沒有實際的經營投資項目、將募集款項用于個人揮霍享樂等行為表現認定其不打算將募集款項返還給投資人,即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投資人投資款項的主觀故意。
與此不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不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在向投資人募集資金時往往具有將募集款項歸還投資人的意思,也具有相應的真實的投資項目,只是可能是后期因項目虧損或者其他風險導致無法歸還投資人款項才引發的糾紛。因此,如果行為人在募集資金時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有真實的投資項目,并將募集來的大部分資金投入該項目,即便是后來出現無法償還投資款項的情形,司法機關在進行定罪處罰時,不應當認定為集資詐騙罪,而應當根據其具體的犯罪情節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者其他犯罪。
其次,除了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一點不同之外,是否使用詐騙方法也是區分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考慮因素之一。
如前所述,“非法占有目的”作為主觀意義上的構成要件,不能僅憑司法工作人員直接的主觀感受予以認定,而必須根據行為人客觀方面的行為予以綜合評判,是否“使用詐騙方法”即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
“使用詐騙方法”可以具體列舉為行為人采取虛構投資項目、進行虛假宣傳許諾以較高的回報率或者將所募集的大部分資金用于個人揮霍享樂的用途等。行為人使用詐騙方法的目的是希望引誘投資人陷入錯誤的處分意思,從而將資金投資給行為人,進而達到將投資款項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集資詐騙罪中“使用詐騙方法”這一要件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具有高度關聯性,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司法機關在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時也會考慮其在行為當時是否使用了詐騙方法,若行為人募集資金是使用了詐騙方法的則其被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也會較大。
但,使用詐騙方法也并非就等同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為了吸引投資者投資會采取夸大投資前景、隱瞞部分事實的手段,行為人的這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尚需綜合案件的具體情況予以綜合判斷,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行為人也有可能采取例如夸大投資效益等欺騙的方法以吸引投資。
再次,除了上述兩點不同之外,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還存在著非法集資款屬性上的區別。
集資詐騙罪侵犯的對象是他人用于集資獲利所交付的集資款,既可以表現為資金,又可以表現為財物;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對象是公眾的存款,只能表現為金錢的形式,并且只能以存款人用于存款而獲取一定利息的形式出現。資金的外延較存款更為寬泛,存款是資金的一種表現形式,除了存款外,資金還包括現金、銀行匯票、銀行本票等其他貨幣資金。我國刑法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對象的范圍限定為“存款”,是從該罪名的保護法益、規范目的所出發的,從目的解釋論的角度來看,該罪名的立法本意是為了保護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存款業務的特許專營權、維護我國金融管理秩序的穩定性,因此將其犯罪對象限定為“存款”,而集資詐騙罪由于其主觀惡性更為嚴重,則將其犯罪對象規定為“資金”。
(二)保護法益不同
集資詐騙罪和詐騙罪是普通法條和特別法條的關系,其所直接想要保護的法益是受害人的個人財產權利,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保護法益則為國家金融管理秩序。
同樣作為非法集資類刑事犯罪,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保護法益上并非是完全割裂的關系,在實際效果上,二者均會起到保護公民個人財產和維護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作用,但從目的解釋論方法出發,非法集資罪的直接立法目的更傾向于保護投資者的個人財產權利,對于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維護則是其附隨性的規范效果和目的;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直接立法目的則更傾向于保護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存款業務的特許專營權、維護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穩定性,在此過程中,雖然也會起到保護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作用,但這也屬于是附隨性的規范效果和目的。
因此,二者在保護法益以及規范效果上存在重疊以及互補的關系,但其側重點會有所不同。
(三)侵犯的信任基礎不同
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保護法益的不同與這兩種犯罪行為所破壞的金融系統中信任基礎的不同也有較大的關聯性,這兩個罪名同屬于金融類犯罪,對其所破壞的信任基礎具體為何要放在金融系統的語境下進行考察。
集資詐騙屬于詐騙的一種形式,其所破壞的是投融資雙方之間一對一的信任關系,盡管司法實踐中集資詐騙罪案件中通常會涉及多名遭受損失的受害投資人,但其在進行投資時系基于對行為人即融資方的人格方面的信任出發處分自己的財產,雙方之間的關系是一對一的信任關系。
而由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要求的犯罪行為具有公開性或社會性的特點,其所破壞的則是投資人基于對社會公眾圍繞金融市場利率和運轉規則形成的一對眾之間的規則信任。存款業務的安全性和穩定性關系國計民生,為了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我國金融管理秩序、存款業務的穩定性,我國對存款業務實施特許經營制度,并對這一業務的相關市場規則予以制度規范化保障,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所破壞的是“公眾”對這一規則的信任,對金融管理秩序以及社會穩定會造成較為嚴重的損害。03區分的意義:實務經驗筆者團隊近期曾辦理了一起當事人涉嫌集資詐騙罪的案件。該案原審判決結果為法院對當事人判處了有期徒刑十年的刑事處罰結果,在筆者團隊接受委托為本案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后,該案在二審中被法院發回重審。筆者團隊經過認真翻閱本案案卷材料、會見本案當事人以及查詢相關法律規定后,認為本案不構成公訴機關指控的集資詐騙罪,而更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理由如下:
1.本案當事人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本案當事人所募集的資金均有明確清晰的去向,均用于返還被害人、公司租賃場地、員工開支等;2.本案當事人并沒有使用詐騙的方法或是虛構相關的項目。涉案的投資項目并非是虛構的,行為人也將募集來的資金實際用于項目的運營,最終無法返還投資款項的原因是因為本案當事人一時經營不善,也沒有故意隱匿財產。
筆者團隊以上述兩點理由為重點,并綜合本案的其他情況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較為完整的法律辯護意見,最終法院接納了筆者團隊提交的辯護意見,對本案當事人認定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非集資詐騙罪,并最終對本案當事人判處有期徒刑兩年三個月。
由此可見,基于對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構成要件、保護法益、所侵犯的信任基礎等方面的區別進行綜合分析,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立法機關在設立這兩個罪名時的立法本意和規范目的,從而能夠更好地分析案件情況,為涉及非法集資類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更好的辯護策略,使其判決結果更符合“以事實為準繩、以法律為依據”的司法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