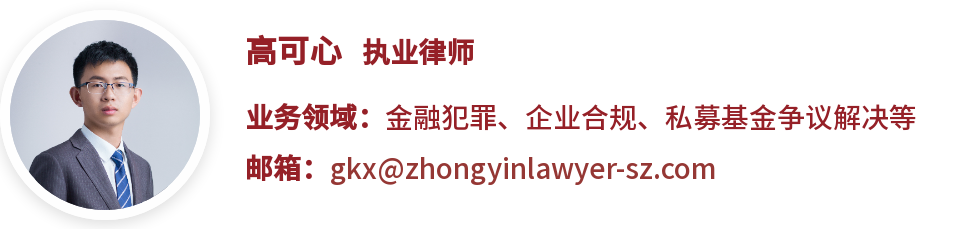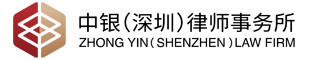摘要:從人類理性指引、感性主義以及實(shí)踐中的可預(yù)見(jiàn)性視角來(lái)看,人工智能符合類似人類的標(biāo)準(zhǔn),故其法律主體資格更應(yīng)作為研究人工智能參與人類生產(chǎn)生活的首要內(nèi)容。從著作權(quán)的角度觀之,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極大沖擊了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體系,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構(gòu)成作品,如構(gòu)成作品,其著作權(quán)應(yīng)當(dāng)歸屬于人工智能開(kāi)發(fā)者還是利用者,目前國(guó)內(nèi)外理論界和實(shí)務(wù)界存在巨大爭(zhēng)議。本文基于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作者主體資格”認(rèn)定現(xiàn)狀的哲學(xué)基礎(chǔ)和理論研究,在人工智能尚未實(shí)現(xiàn)意志自由的背景下,試圖探討“擬制作者”規(guī)則的可行性。
關(guān)鍵詞: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擬制作者
目錄
一、人工智能應(yīng)用背景下的著作權(quán)法律主體資格理論研究
二、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國(guó)際立法研究
三、人工智能“作者主體資格”認(rèn)定的現(xiàn)實(shí)考量
四、我國(guó)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規(guī)定及生成物的現(xiàn)實(shí)認(rèn)定
五、總結(jié)
一、人工智能應(yīng)用背景下的著作權(quán)法律主體資格理論研究
1956年約翰·麥卡錫等人在達(dá)特茅斯發(fā)起的“人工智能”會(huì)議上,將人工智能定義為“通過(guò)機(jī)器模擬人的智能”。按照此定義,人工智能是通過(guò)計(jì)算機(jī)系列算法和機(jī)器實(shí)體形成的共同體。2022年11月,ChatGPT4.0橫空出世,雖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聊天機(jī)器人,“具有”獨(dú)立思考的能力,但其本質(zhì)仍是大腦的思維實(shí)踐性和存在實(shí)體性的結(jié)合。
人工智能出現(xiàn)之后,有關(guān)其法律主體資格的爭(zhēng)論就異常激烈。此后關(guān)于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主體資格的問(wèn)題甚囂塵上,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乃至整個(gè)司法領(lǐng)域都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難以直接定論。針對(duì)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的法律人格問(wèn)題,當(dāng)前法學(xué)理論界的主流觀點(diǎn)認(rèn)為,民法中的人格自古羅馬法延續(xù)至今始終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擴(kuò)張式的變遷衍化態(tài)勢(shì),突破人類中心主義思維局限,承認(rèn)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乃是民法人格理論發(fā)展的勢(shì)之所趨,然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是否具有主體資格地位應(yīng)視其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和人格權(quán)益予以劃分。
判斷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著作權(quán)法律主體資格,應(yīng)當(dāng)要了解人工智能法律主體資格的內(nèi)容和邊界,故本文將“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法律主體資格”放在“人工智能主體資格”這一框架下進(jìn)行研究。討論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主體地位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是人工智能是否被允許產(chǎn)生自我意識(shí)。在自我意識(shí)進(jìn)化上,寫(xiě)作機(jī)器人可能是目前所有人工智能中最前沿的。若賦予寫(xiě)作機(jī)器人自我激發(fā)創(chuàng)作靈感及創(chuàng)作行為的能力,允許機(jī)器人自我激發(fā)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進(jìn)而自主進(jìn)行人物設(shè)定、場(chǎng)景選擇、情節(jié)演進(jìn)等創(chuàng)作,人工智能寫(xiě)作機(jī)器人已可被視為獨(dú)立創(chuàng)作主體。現(xià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界依據(jù)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我意識(shí)對(duì)其主體資格大致可劃分為兩種陣營(yíng):主體說(shuō)和客體說(shuō)。主體說(shuō)統(tǒng)一認(rèn)為人工智能應(yīng)當(dāng)被賦予法律人格,承認(rèn)并賦予機(jī)器人的權(quán)利主體地位,既是權(quán)利發(fā)展的內(nèi)在規(guī)律,也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必然趨勢(shì),但是關(guān)于其擁有權(quán)利的范圍和涵義上并不相同。故在主體說(shuō)陣營(yíng)中逐漸派生為“有限人格說(shuō)”和“擬制人格說(shuō)”兩種學(xué)說(shuō)。
(一)有限人格說(shuō)
“有限人格說(shuō)”認(rèn)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是在其享有權(quán)利并承擔(dān)責(zé)任,可以做出獨(dú)立自主行為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但并不是完全獨(dú)立的,其享有的法律人格是有限的,這是由其本質(zhì)上的工具屬性導(dǎo)致的。許中緣和袁曾的觀點(diǎn),都是從人工智能權(quán)利義務(wù)和行為責(zé)任能力的有限性出發(fā),對(duì)人工智能人格的有限性進(jìn)行論證。理論界袁曾的“擬制(次等)法律人格說(shuō)”、張磊的“位格加等說(shuō)”、張紹欣的“人格類比說(shuō)”與前述觀點(diǎn)無(wú)實(shí)質(zhì)差異。
該學(xué)說(shuō)反映到著作權(quán)領(lǐng)域,其核心要義有三,一是有獨(dú)立的意思形成能力和表示能力。當(dāng)下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識(shí)在不斷增強(qiáng),能夠創(chuàng)造出獨(dú)特的作品,可以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獨(dú)立的主體。事實(shí)上,人工智能已經(jīng)不再是人類進(jìn)行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一種工具,它開(kāi)始具備了行使獨(dú)立創(chuàng)造行為的能力,人工智能已經(jīng)開(kāi)始和人腦智能傳統(tǒng)科學(xué)技術(shù)相等甚至更為高級(jí)。二是人工智能可以借助于法律人格承擔(dān)權(quán)利義務(wù)。以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為例,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反映的是作者依靠作品享有經(jīng)濟(jì)收益權(quán),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可轉(zhuǎn)讓或繼承。但人工智能只能通過(guò)法定主體,通常是自然人、法人等行使出租權(quán)、發(fā)行權(quán)等,其本身無(wú)法直接行使。故賦予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主體地位,符合權(quán)利發(fā)展規(guī)律,是科技與社會(huì)實(shí)力提升的結(jié)果。三為“有限”人格,基于法律制度的缺失,暫不宜直接賦予其完全獨(dú)立的法律人格,考慮到其承擔(dān)法律行為后果的有限性,可在人工智能與自然人之間進(jìn)行權(quán)利的劃分,將部分權(quán)利作為自然人的保留性權(quán)利。人工智能是無(wú)法取得與自然人在著作人身權(quán)上的同等地位的。例如,目前人工智能本身還無(wú)法獨(dú)立進(jìn)行修改活動(dòng)。假若法律上認(rèn)同了其修改權(quán),實(shí)踐中可能發(fā)生使用人對(duì)其工具產(chǎn)物進(jìn)行修改還要征得人工智能軟件本身同意的情況,如此會(huì)產(chǎn)生邏輯混亂。
(二)擬制人格說(shuō)
“擬制人格說(shuō)”認(rèn)為,人工智能具有思維能力而脫離傳統(tǒng)的“物”的范疇,但是人工智能本質(zhì)上的工具屬性未能改變。在此情境下,通過(guò)法律擬制的方法來(lái)解決人工智能權(quán)利來(lái)源上的技術(shù)性問(wèn)題,同法人一樣,賦予新主體相同或類似的法律地位,對(duì)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尚不宜以成文法的形式予以明確規(guī)定,而適宜“以實(shí)定法解釋論為基礎(chǔ),在堅(jiān)持人工智能為客體的原則下,運(yùn)用擬制的法律技術(shù),將特定情形下的人工智能認(rèn)定為法律主體,從而為應(yīng)對(duì)、引領(lǐng)未來(lái)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奠定法律主體基礎(chǔ)”。比如陳吉棟認(rèn)為,處理人工智能主體立法抉擇的基本原則為法律不應(yīng)介入人工智能的技術(shù)黑洞。楊清望、張磊則從人工智能的自身屬性、價(jià)值指向、應(yīng)用路徑和責(zé)任承擔(dān)等方面詳細(xì)闡述了擬制人格的現(xiàn)實(shí)性和必要性。該學(xué)說(shuō)的理論依據(jù)為: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是漸進(jìn)式的,與現(xiàn)代民法中的法人制度較為相似,自“否認(rèn)說(shuō)”過(guò)渡至“擬制說(shuō)”,直至“實(shí)在說(shuō)”。另外,現(xiàn)代司法制度具有包容性,即對(duì)人工智能以非“工具式”的立場(chǎng)予以考量。
回歸到著作權(quán)領(lǐng)域,目前的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雖然具有人類智力創(chuàng)作成果的表象,但其屬于由特定系統(tǒng)、算法運(yùn)行后得到的產(chǎn)物。以ChatGPT為例,ChatGPT是基于Transformer架構(gòu)的預(yù)訓(xùn)練語(yǔ)言模型,擁有語(yǔ)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還能根據(jù)聊天的上下文進(jìn)行互動(dòng)。其根本上是利用人工智能軟件做成的生成模型,一旦離開(kāi)數(shù)據(jù)標(biāo)注員的參數(shù)標(biāo)注和訓(xùn)練員的文本數(shù)據(jù)輸入,模型不可能生成任何其他類型的新作品。此外,文心一言的“個(gè)性化表達(dá)”也非 AI 本身的個(gè)性化體現(xiàn),而是創(chuàng)作者對(duì)大模型訓(xùn)練的特定體現(xiàn)。就“創(chuàng)”而言,人工智能生成成果可以很好地滿足客觀主義下的“最低限度創(chuàng)造”的形式要求。因此,新一代大模型在客觀主義下不存在顯著的創(chuàng)造性障礙。但是,當(dāng)前我國(guó)對(duì)獨(dú)創(chuàng)性之“創(chuàng)”還存在隱含的價(jià)值判斷,這一點(diǎn)在學(xué)界和司法實(shí)踐中十分顯見(jiàn)。價(jià)值判斷的本質(zhì)是對(duì)作品內(nèi)涵一定思想深度的要求,新一代大模型的生成本質(zhì)是參數(shù)標(biāo)注與概率計(jì)算,由于其不具備人類思想因此不可能滿足一定思想深度的潛在要求,進(jìn)而難以符合價(jià)值判斷要件。然基于人工智能在社會(huì)發(fā)展中參與角色的復(fù)雜性和廣泛性,可以依照法人制度賦予人工智能新的主體資格,通過(guò)評(píng)估人工智能在著作完成過(guò)程中的參與程度的多少,根據(jù)不同情況來(lái)分配著作權(quán):人工智能作為輔助工具時(shí)使用者享有著作權(quán)、人工智能和人類共同完成著作時(shí)二者共享著作權(quán),人工智能自己獨(dú)立進(jìn)行發(fā)明創(chuàng)造則人工智能單獨(dú)擁有著作權(quán)。
(三)客體說(shuō)
在“客體說(shuō)”看來(lái),尤其是反對(duì)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主體的學(xué)者認(rèn)為人工智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復(fù)制人類思維和模擬大腦意識(shí),其活動(dòng)只是被動(dòng)地適應(yīng)環(huán)境、做出選擇,它不是通過(guò)實(shí)踐活動(dòng)對(duì)外部世界進(jìn)行認(rèn)識(shí)和改造的真正主體。吳漢東和劉洪華認(rèn)為,法律人格的核心在于自然人和自然人集合體的意志能力,人工智能的行為還是受制于民事主體的控制,還沒(méi)有發(fā)展到擁有理性,其工具屬性未曾改變,還不能取得獨(dú)立的主體地位,但可以作為特殊的“物”,通過(guò)法律客體得到保護(hù)。龍文懋和曹新明則分別從法哲學(xué)和倫理角度論證人工智能不能成為法律主體,基于人工智能不是“欲望主體”和“主體風(fēng)險(xiǎn)”等考量,堅(jiān)決否認(rèn)人工智能成為法律主體的可能性,堅(jiān)定將人工智能置于法律客體的地位。楊立新提出,應(yīng)將人工智能的主體地位界定為“人工類人格”,是一種人工創(chuàng)造地接近自然人人格的民事法律地位,但實(shí)質(zhì)上仍屬于物的范疇,又區(qū)別于其他的“物”。
然而,現(xiàn)今根據(jù)“思想與表達(dá)二分法“的原則,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作品的表現(xiàn)形式而非思想本身,因此無(wú)需一定要求作品能夠抒發(fā)人類情感的高度或體現(xiàn)創(chuàng)作者的人格屬性,也即,只要人工智能“獨(dú)立”生成的作品客觀上能夠滿足最低程度的創(chuàng)造性,具備流暢的情節(jié)內(nèi)容、完整的邏輯結(jié)構(gòu)等要素,在表現(xiàn)形式上與人類作品無(wú)異,即能夠帶給閱讀或欣賞者以一定的感受,就應(yīng)當(dāng)認(rèn)可其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給予其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上的保護(hù)。
當(dāng)下階段需要重點(diǎn)討論的是人工智能原創(chuàng)性的虛構(gòu)創(chuàng)作。隨著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的規(guī)模運(yùn)用,跨語(yǔ)義空間的多個(gè)深度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模型實(shí)現(xiàn)了針對(duì)圖片的多領(lǐng)域和情感維度的深度優(yōu)化。如微軟小冰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非由人工激發(fā),而是通過(guò)圖片進(jìn)行意象激發(fā)。小冰等已經(jīng)具備類人類大腦思維,具有了一定的人格化抒情詩(shī)創(chuàng)作能力,有其自身“傷感時(shí)代”風(fēng)格。從現(xiàn)實(shí)分析,當(dāng)下人工智能寫(xiě)作機(jī)器人已經(jīng)具備獨(dú)立創(chuàng)作高水平原創(chuàng)作品的能力。這就更加需要重點(diǎn)檢視人工智能寫(xiě)作機(jī)器人是否擁有作者主體資格。
綜合上述觀點(diǎn),無(wú)論是基于“客體說(shuō)”,還是“主體說(shuō)”,用馬克思主義觀點(diǎn)來(lái)分析,人的主體地位是在認(rèn)識(shí)和改造外部世界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中形成,并通過(guò)實(shí)踐活動(dòng)體現(xiàn)并確證人的能動(dòng)性、創(chuàng)造性和社會(huì)性。在這個(gè)意義上,人工智能無(wú)法復(fù)制、模擬和超越人類主體性。因此,主張“法律人格”的界定并不只是法律問(wèn)題,還涉及倫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問(wèn)題,法律的外衣并不能理所當(dāng)然地對(duì)各種事物冠以“人格權(quán)”,即使法律擬制能夠設(shè)定缺乏倫理依據(jù)的“人格權(quán)”,也還需要對(duì)是否有必要賦予人工智能人格權(quán)充分的論證。
二、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國(guó)際立法研究
縱觀各國(guó)法律,盡管其關(guān)于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的規(guī)定都有自己的內(nèi)在文化屬性和現(xiàn)實(shí)考量,但總體來(lái)看不存在絕對(duì)的差距。
2016年,日本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促進(jìn)計(jì)劃》指出,人工智能開(kāi)發(fā)商和用戶不能根據(jù)版權(quán)法預(yù)先行使其權(quán)利,人工智能亦不是創(chuàng)作主體;英國(guó)法律明確賦予計(jì)算機(jī)生成內(nèi)容與人類作品同等地位,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定義為“在沒(méi)有自然人創(chuàng)作的情況下由計(jì)算機(jī)創(chuàng)作的作品”。
2016年5月,歐盟議會(huì)法律事務(wù)委員會(huì)在其向歐盟委員會(huì)提交的《就機(jī)器人民事法律規(guī)則向歐委會(huì)提出建議的報(bào)告》中,建議歐盟委員會(huì)考慮在未來(lái)的立法中賦予最高端的智能機(jī)器人電子人地位(status of electronic persons),使其為自己的致害行為承擔(dān)責(zé)任,并在自主做決定或獨(dú)立與第三人互動(dòng)時(shí)利用其電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ality)。
2017年,俄羅斯民法學(xué)者完成法律草案《在完善機(jī)器人領(lǐng)域關(guān)系法律調(diào)整部分修改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的聯(lián)邦法律》(又稱《格里申法案》)第1條中,提出了賦予機(jī)器人“機(jī)器人-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建議,規(guī)定“機(jī)器人-代理人”擁有獨(dú)立的財(cái)產(chǎn)并以之為自己的債務(wù)承擔(dān)責(zé)任,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取得并行使民事權(quán)利和承擔(dān)民事義務(wù)。雖然該草案只是俄羅斯學(xué)者對(duì)機(jī)器人和機(jī)器人—代理人在私法框架內(nèi)形成的初步認(rèn)識(shí)與規(guī)范設(shè)計(jì),但其卻是世界上最早的關(guān)于智能機(jī)器人法律地位的法律草案之一。
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二條規(guī)定,中國(guó)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是中國(guó)法定著作權(quán)主體,人工智能不在其列。同樣,美國(guó)版權(quán)局在“猴子自拍照”版權(quán)登記案后也明確表示只保護(hù)人類創(chuàng)作作品,排除機(jī)器生成作品,甚至是對(duì)機(jī)器純自動(dòng)或隨機(jī)產(chǎn)生、不依靠自然人作者干預(yù)生成的作品也不予版權(quán)保護(hù)。此外,2018 年美國(guó)版權(quán)局在審查“天堂入口”這一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的作品的注冊(cè)版權(quán)的復(fù)議請(qǐng)求時(shí)又重申: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不能被授予版權(quán)。2023年3月,美國(guó)版權(quán)局同樣表示 Midjourney生成的漫畫(huà)小說(shuō)中圖像不被版權(quán)登記與保護(hù)。由引可知,中美兩國(guó)都不支持對(duì)人工智能生成作品進(jìn)行著作權(quán)法或版權(quán)法保護(hù)。
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角度看,了解人類法律主體制度的文化屬性,需在人類歷史的哲學(xué)基礎(chǔ)上進(jìn)行探討,人類理性首先在于人類具有先天性的認(rèn)知機(jī)能,是一個(gè)能動(dòng)的認(rèn)知主體。近代西方哲學(xué)創(chuàng)始人笛卡爾從理性主義認(rèn)識(shí)論出發(fā)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題,開(kāi)啟了哲學(xué)研究向主體性哲學(xué)的轉(zhuǎn)向,如黑格爾所言:“從笛卡爾起,我們踏進(jìn)了一種獨(dú)立的科學(xué)。這種哲學(xué)明白:它自己是獨(dú)立地從理性而來(lái)的,自我意識(shí)是真理的主要環(huán)節(jié)。黑格爾的“絕對(duì)精神”更是主張“需要精神通過(guò)正—反—合的辯證法運(yùn)動(dòng),從而分階段地把種種事物實(shí)現(xiàn)出來(lái)”。理性、思維、理念是主體的首要特質(zhì),而感性、身體、靈魂、心靈等則處于從屬地位,這成為近代哲學(xué)對(duì)于人類主體的基本建構(gòu)圖式。而在康德“主客體統(tǒng)一認(rèn)識(shí)論”和“人是目的”哲學(xué)視點(diǎn)下,無(wú)論人工智能發(fā)展到何種階段,都只能作為人利用的客體和工具處理,而不能將其擬制為與人享有平等地位的法律主體。
目前,人工智能高度自主,并有不斷脫離人類控制的趨勢(shì),似乎具有“精神、意識(shí)”的人工智能應(yīng)當(dāng)被賦予法律主體地位已成為一個(gè)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當(dāng)“精神、意識(shí)”不再為人類所獨(dú)享,似乎“主客體之間這種不可逾越的鴻溝”發(fā)生動(dòng)搖也是不可逆轉(zhuǎn)的趨勢(shì)。
三、人工智能“作者主體資格”認(rèn)定的現(xiàn)實(shí)考量
從實(shí)踐角度來(lái)看,奧地利1988年《民法典》285A 條規(guī)定:動(dòng)物不是物,它們受特別法的保護(hù)。人類對(duì)動(dòng)物的利用難以避免,但人類把關(guān)注動(dòng)物的生存狀況視作道德進(jìn)步,因?yàn)閯?dòng)物在某些方面具有類人性。正是此種共識(shí),人類普遍接受將動(dòng)物當(dāng)作特別物,動(dòng)物是部分擁有類人主體性的特殊主體。基于此,人工智能機(jī)器人存在“不是物”的立法需求,該類機(jī)器人不是普通物,它具有思維性,是擁有部分主體性的特殊主體。那么,人類是否可給予其特殊主體地位呢?“法律上的主體資格一般來(lái)源于行為能力、責(zé)任能力、權(quán)利能力,機(jī)器人具有行為能力、責(zé)任能力。”人工智能機(jī)器人若被視為普通物,其權(quán)利能力由其擁有者“人”代行——這也是熊琦教授的觀點(diǎn)。此觀點(diǎn)受限于當(dāng)前著作權(quán)法,對(duì)作者主體的理解過(guò)于狹窄,拒絕認(rèn)定人工智能機(jī)器人的作者主體地位。
2016年2月,美國(guó)國(guó)家公路安全交通管理局認(rèn)定谷歌無(wú)人駕駛汽車系統(tǒng)可被視為“司機(jī)”,從實(shí)踐角度賦予人工智能機(jī)器人部分主體資格。討論人工智能寫(xiě)作機(jī)器人主體地位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是機(jī)器人是否被允許產(chǎn)生自我意識(shí)。在自我意識(shí)進(jìn)化上,寫(xiě)作機(jī)器人可能是目前所有人工智能中最前沿的。若賦予寫(xiě)作機(jī)器人自我激發(fā)創(chuàng)作靈感及創(chuàng)作行為的能力,允許機(jī)器人自我激發(fā)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進(jìn)而自主進(jìn)行人物設(shè)定、場(chǎng)景選擇、情節(jié)演進(jìn)等創(chuàng)作,人工智能寫(xiě)作機(jī)器人已可被視為獨(dú)立創(chuàng)作主體。目前主要的機(jī)器人寫(xiě)作運(yùn)營(yíng)領(lǐng)域?yàn)闄C(jī)器人新聞?dòng)浾撸缆?lián)社的 WordSmith、華盛頓郵報(bào)的 Heliograf、紐約時(shí)報(bào)的Blossom、新華社的快筆小新、騰訊的 Dreamwriter,均為這類機(jī)器人。多數(shù)機(jī)器人記者采寫(xiě)的稿件,均得到了標(biāo)注或者直接署名,至少?gòu)氖鹈麢?quán)分析,該類寫(xiě)作機(jī)器人已部分地?fù)碛小白髡咧黧w資格”。
人工智能通常會(huì)自動(dòng)檢索并拾取無(wú)版權(quán)糾紛的數(shù)據(jù),且依靠目前的數(shù)據(jù)算法和算力,監(jiān)管監(jiān)測(cè)者還無(wú)法判斷生成內(nèi)容侵權(quán)與否。另一方面,其權(quán)利的享有和義務(wù)的承擔(dān)根本無(wú)法實(shí)現(xiàn)。人工智能本身無(wú)法作為法定民事訴訟主體,皆是由自然人或法人、非法人組織來(lái)處理侵權(quán)事宜。然而,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與人類創(chuàng)作內(nèi)容在區(qū)分上存在一定的困難,如果公眾將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作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很有可能會(huì)擾亂當(dāng)前的著作權(quán)法律秩序。
四、我國(guó)人工智能著作權(quán)規(guī)定及生成物的現(xiàn)實(shí)認(rèn)定
我國(guó)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第三條規(guī)定:“本法所稱的作品,是指文學(xué)、藝術(shù)和科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xiàn)的智力成果”。由此可見(jiàn),受到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的作品需要同時(shí)滿足以下三點(diǎn):(1)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2)屬于文學(xué)、藝術(shù)、科學(xué)領(lǐng)域;(3)能夠以一定形式表現(xiàn)的智力成果。根據(jù)該條款的定義,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必須具備“獨(dú)創(chuàng)性”“有形性”“可復(fù)制性”與“智力成果”四個(gè)要件,才能構(gòu)成著作權(quán)法所保護(hù)的作品。而現(xiàn)行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是以人類智力為中心來(lái)構(gòu)建其保護(hù)對(duì)象,因此上述“智力成果”應(yīng)當(dāng)特指人類經(jīng)過(guò)創(chuàng)造性勞動(dòng),滿足“額頭出汗”原則所創(chuàng)作形成的智力成果。有學(xué)者認(rèn)為,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是應(yīng)用算法和模板的同質(zhì)化產(chǎn)物,其生成內(nèi)容的過(guò)程與自然人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有本質(zhì)區(qū)別,因而不能定義為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上的“作品”。然北京互聯(lián)網(wǎng)法院近日針對(duì)人工智能生成圖片(AI繪畫(huà)圖片)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糾紛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時(shí)認(rèn)定:“人們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圖片時(shí)……本質(zhì)上仍然是人利用工具進(jìn)行創(chuàng)作,即整個(g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進(jìn)行智力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鼓勵(lì)創(chuàng)作,被公認(rèn)為著作權(quán)制度的核心目的……人工智能生成圖片,只要能體現(xiàn)出人的獨(dú)創(chuàng)性智力投入,就應(yīng)當(dāng)被認(rèn)定為作品,受到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然而,法院忽視了能夠體現(xiàn)原告智力投入的模型選擇、提示詞的選擇和生成參數(shù)的設(shè)置僅僅屬于思想,對(duì)上述思想的個(gè)性化選擇和判斷不足以使人工智能生成的圖片在表達(dá)上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與傳統(tǒng)創(chuàng)作工具相比,人工智能使用者在內(nèi)容生成中只起到間接影響作用,沒(méi)有實(shí)施創(chuàng)作行為,人工智能基本取代了人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所以人工智能并非人創(chuàng)作的工具。
就目前國(guó)內(nèi)司法實(shí)踐而言,人工智能不具有主體資格,因此不是著作權(quán)法上的作者、不是著作權(quán)人。但人工智能生成物已經(jīng)可以被認(rèn)定為著作權(quán)的客體,就該客體目前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而言,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構(gòu)成著作權(quán)上作品,歸根結(jié)底要看人工智能使用人對(duì)生成物的產(chǎn)生是否直接投入了智力性勞動(dòng)以及智力貢獻(xiàn)度。如果生成物完全由人工智能獨(dú)立完成,或者使用人未直接投入任何智力性活動(dòng)、使用人的智力貢獻(xiàn)度為零,生成物不構(gòu)成著作權(quán)上的作品,使用人就生成物也不應(yīng)享有著作權(quán)法上的權(quán)利。如果生成物完全由使用人獨(dú)立完成,人工智能只是替代使用人或者輔助使用人完成一些非智力性勞動(dòng),生成物可以構(gòu)成著作權(quán)上的作品,使用人就生成物可以享有著作權(quán)法上的權(quán)利。
五、總結(jié)
社會(huì)是發(fā)展變化著的,但法律無(wú)法時(shí)刻反映出社會(huì)的變化。面對(duì)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對(duì)建立在傳統(tǒng)科技條件下的著作權(quán)法所造成的沖擊,我們應(yīng)當(dāng)重新審視和詮釋著作權(quán)法,回歸著作權(quán)法的立法本位,平衡好各項(xiàng)權(quán)利的權(quán)利人之間的利益分配。在作品創(chuàng)作逐漸呈現(xiàn)人工智能化和工具化的背景下,我們也更應(yīng)當(dāng)從真正實(shí)現(xiàn)作品創(chuàng)作和利用的世俗、平等和自由角度,來(lái)解讀既有著作權(quán)法規(guī)則。
當(dāng)下,人工智能尚未能實(shí)現(xiàn)人格獨(dú)立和意志自由,依舊是作為人利用的客體和工具處理,即能夠被認(rèn)定為人類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工具。在世界各國(guó)主流的著作權(quán)法框架下,作者資格的認(rèn)定限于人類。隨著人工智能的飛速發(fā)展,借鑒“擬制作者”規(guī)則將人工智能本身認(rèn)定為作者,使作者的主體資格突破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限制便顯得尤為重要。現(xiàn)行的著作權(quán)法框架已逐漸無(wú)法解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認(rèn)定與著作權(quán)歸屬的問(wèn)題,但該問(wèn)題的解決又關(guān)乎人工智能倫理和法律主體變動(dòng)的討論。用溫德?tīng)枴ね呃蘸涂屏帧ぐ瑐惖摹暗赖聶C(jī)器”觀點(diǎn)來(lái)看,解決終極的人工智能倫理問(wèn)題還很遙遠(yuǎn),但需要朝著這個(gè)方向走。
參考文獻(xiàn)
[1] 徐文:反思與優(yōu)化:人工智能時(shí)代法律人格賦予標(biāo)準(zhǔn)論[J]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7):2-4。
[2] 余德厚:從主體資格到權(quán)責(zé)配置:人工智能法學(xué)研究視角的轉(zhuǎn)換[J].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2020,40(06):176-185。
[3] 許中緣:論智能機(jī)器人的工具性人格[J].法學(xué)評(píng)論 ,2018,036(005):153-164。
[4] 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審視[J].東方法學(xué),2017,000(005):50-57。
[5] 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審視[J].東方法學(xué),2017,(5):5-8。
[6] 楊清望,張磊:論人工智能的擬制法律人格[J].湖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6):3-5。
[7] 張紹欣:法律位格、法律主體與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J].現(xiàn)代法學(xué),2019,(4):3-4。
[8] 張玉潔:論人工智能時(shí)代的機(jī)器人權(quán)利及其風(fēng)險(xiǎn)規(guī)制[J].東方法學(xué),2017(06):56-66。
[9] 易繼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是作品嗎?[J].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7,35(05):137-147。
[10] 陳吉棟:論機(jī)器人的法律人格—基于法釋義學(xué)的討論[J].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3):2-3。
[11] 陳吉棟:論機(jī)器人的法律人格——基于法釋義學(xué)的討論[J].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35(03):78-89。
[12] 楊清望,張磊:論人工智能的擬制法律人格[J].湖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21(006):91-97。
[13] 華宇元典法律人工智能研究院:讓法律人讀懂人工智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2,第23頁(yè)。
[14]吳漢東: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權(quán)法之問(wèn)[J].中外法學(xué),2020,32(03):653-673。
[15] 劉洪華:論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J ].政治與法律,2019,284(01):11-21。
[16] 龍文懋:人工智能法律主體地位的法哲學(xué)思考[J].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8,36(05):24-31。
[17] 曹新明,咸晨旭:人工智能作為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主體的倫理探討[J].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0,50(01):94-106。
[18] 楊立新:人工類人格:智能機(jī)器人的民法地位——兼論智能機(jī)器人致人損害 的民事責(zé)任[J].求是學(xué)刊 ,2018,45(04):84-96。
[19] 慕曉琛: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quán)歸屬之域外法研究——以英國(guó),美國(guó),歐 盟和澳大利亞為例[J].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2019(8):10。
[20] 黑格爾:哲學(xué)史講演錄(第四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wù)印書(shū)館 1959 年版,第59 頁(yè)。
[21] 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xiàn)代民法,《中外法學(xué)》1997年第2期,第6頁(yè)。
[22] 楊學(xué)科:論人工智能機(jī)器人權(quán)利及其權(quán)利界限,《天府新論》2019 年第1期,第9-11頁(yè)。
[23] 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的著作權(quán)認(rèn)定,《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2017年第3期,第5-6頁(yè)。
律師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