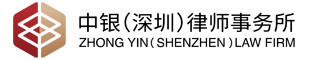相對于專利、商標和著作權業務,植物新品種案件屬于知識產權實務中相對“冷門”的板塊,植物新品種案件中涉及的專業性問題也未能獲得足夠的關注。司法案例中體現出的審判思路以及法院對爭議問題的闡明也沒有引起重視。高景賀律師作為在植物新品種司法保護耕耘十余年的專業律師,分析司法實務中的相關問題,既是因“事實與規范之間穿梭往返”的職業習慣的使然,也是因“促進育種創新、推動種業發展”的行業使命的召喚。本文基于植物新品種案件訴訟實務的邏輯,結合2007年品種權司法解釋出臺后的代表性案例,對值得關注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梳理,以期能見拋磚之效,助力植物新品種的司法保護。文章內容較多,分為系列文推送,本次推送為第二篇,主要涉及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后期精彩內容請關注深圳中銀律師事務所公眾號。往期系列文章請點擊文末相關鏈接。
三、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訴什么)
1、UPOV公約對品種權保護范圍的界定
一直以來,國際上對植物新品種權保護范圍的界定就存在爭議,有人認為,收獲材料(包括使用繁殖材料獲得的整株植物和植物的部分),植物本身以及為嫁接和繁殖新植物而被切斷的枝條、接穗,都應當作為繁殖材料給予保護;也有人認為,應包括植物的任何材料等。UPOV公約78文本中將品種權的保護范圍限定在“有性或無性繁殖材料”和“無性繁殖材料應包括植物整株”兩個方面。[1] UPOV公約91文本則將由繁殖材料延伸至了收獲材料及直接制成品。[2]
2、我國對品種權保護范圍的討論
對于我國品種權保護范圍,有觀點認為品種權保護范圍的界定涉及科學技術理論問題,不是司法機關單獨所能解決的,但就某些記載新品種特異性的授權機關的書面審査材料,在與授權機關達成共識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先行解釋作為侵權判定的證據使用。[3]還有觀點認為,品種權的保護范圍應當是授權品種的特異性。[4]《司法解釋》征求意見時,林業和農業的主管部門也有不同意見,前者認為應以審批機關批準的品種權申請文件記載的特異性為保護范圍,而后者則主張申請品種的全部遺傳特性都包含在繁殖材料中,應以繁殖材料來確定品種權保護范圍。[5]《司法解釋》初稿也曾經基于專利權與品種權最為接近的考慮,擬借鑒專利侵權的認定方法,但因植物品種是活體,以繁殖材料為載體的生物遺傳特性難以用文字全面、準確地描述,無法清楚地劃定品種權的效力范圍,故無法采用專利侵權判定的“三步走”方法,[6]司法解釋最終以被控侵權繁殖材料與授權品種具有相同特征特性作為比對標準進行侵權認定,而并未直接規定品種權的保護范圍是什么。[7]
3、司法實踐對品種名稱權的探索
一般認為植物新品種權屬于創造性智力成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是具備生命自繁特征的東西,[8]繁殖材料是植物生命遺傳信息的自然表達。[9]新品種的植物生命遺傳特性體現在繁殖材料上,品種侵權聚焦在授權繁材上。[10]品種權名稱僅是獲得授權的前提條件、維持品種的存續要素和品種管控手段,但品種名稱并未包含在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內,成為品種權的一部分。[11]然而,立法上,植物新品種的繁殖材料與品種權名稱實現了有機統一。[12]UPOV 公約和《種子法》均規定,品種權名稱用于識別品種,[13]在不同品種之間,品種權名稱具有唯一性——相同近似品種品名應相區別;在不同階段(時期),品種權名稱具有同一性——審定、授權、登記、推廣、銷售同一;在時空范圍上,載體(繁殖材料)與指代(品種權名稱)上具有統一性;[14]在具體使用上,品種權名稱與其他標記連用時具有突出性——與商標連用時要突出品名。[15]實務中,權利人實際支配和控制著繁殖材料和品種名稱的兩個部分的利用,[16]植物新品種侵權行為往往涉及繁殖材料和品種名稱兩個部分。[17]因品種權名稱傳遞著新品種的種質特性、信譽和育種者身份等信息,[18]品種權名稱成為品種侵權核心方式和重要環節。[19]實踐中,非法利用品種權名稱經營獲利的糾紛頻發且樣式繁雜,從“曾用名銷售”[20]到“變名銷售”,[21]再到“品名商標化銷售”,[22]甚至“數字簡稱銷售”不一而足,“一品多名、一名多品”[23]現象似成為假冒侵權套牌等植物新品種侵權行為泛濫的直接根源。[24]為解決前述問題,開始有了通過品種權名稱保護品種權的路徑探索。典型代表為河南高院裁定“因品種權名稱被不正當使用而請求判令被告停止相應的侵權行為并承擔民事責任的案件,屬于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移送至鄭州法院審理[25]以及審判法官發表的品種名稱保護系列文章。[26]
4、我國有關品種權保護范圍的最新案例
我國司法實踐從未停止對于品種權保護范圍界定的探索。在蔡某光、廣州市潤平商業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27]最高院認為,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與繁殖材料密切相關,繁殖材料目前作為我國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是品種權人行使獨占權的基礎。將品種的繁殖材料規定為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是因為品種的遺傳特性包含在品種的繁殖材料中。繁殖材料在形成新個體的過程中進行品種的繁衍,傳遞了品種的特征特性,遺傳信息通過繁殖材料實現了代代相傳,表達了明顯有別于在申請書提交之時已知的其他品種的特性,并且經過繁殖后其特征特性未變。雖然繁殖材料包括有性繁殖材料和無性繁殖材料,植物或植物體的一部分均有可能成為繁殖材料,但其是否屬于植物新品種權保護范圍的繁殖材料,有賴于所涉植物體繁殖出的植物的一部分或整個植物的新的個體,是否具有與該授權品種相同的特征特性。植物新品種權保護范圍的認定屬于法律適用問題,應當以品種權法律制度為基礎進行分析。[28]
5、認定繁殖材料的考量因素
(1)在界定繁殖材料的范圍時,品種實際栽培時采用的與產品定價相符的常規繁殖技術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使用特殊的繁殖方式,比如采用組培、細胞培養等手段時,其成本是否能夠支撐商品利潤,是否能夠在實際生產中大范圍應用,應當是繁殖材料的范圍界定時應當考慮的重要因素。[29]
(2)繁殖材料因植物品種的不同呈現出形態差異。農業品種前者主要指可繁殖植物的種植材料或植物體的其他部分,包括籽粒、果實和根、莖、苗、芽、葉等,以有性繁殖的大田作物居多;林業品種主要是指整株植物(包括苗木)、種子(包括根、莖、葉、花、果實等)以及構成植物體的任何部分(包括組織、細胞),以無性繁殖的園藝花卉、果樹林木為主。
(3)雜交種的繁殖材料并不是雜交種本身,而是其親本(父本和母本)。雜交種是通過不同親本 (父本 、母本 )經過特定的組合方式得到的第一子代(F1),其第二子代(F2)會發生遺傳變異,在特征特性上與雜交種都有不同,且雜交種本身不具有育種學上的可繁殖性,故“雜交種繁殖材料就是F1代雜交種的種子,而不是用于培育雜交種品種的親本(包括父本和母本)”觀點[30]并不可取。
(4)植物品種涉及的材料分為繁殖材料、收獲材料以及直接由收獲材料制成的產品。作為目前植物新品種權保護范圍的繁殖材料,應當是具有繁殖能力的活體,且能夠繁殖出與授權品種具有相同的特征特性的新個體。授權品種的保護范圍不受限于申請植物新品種權時采取的特定方式獲得的繁殖材料。當不同于授權階段繁殖材料的植物體已為育種者所普遍使用時,該種植材料應當作為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納入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范圍。[31]
注釋:
[1] UPOV Convention(1978 Act), Article 5
[2] UPOV Convention(1999 Act), Article 14(2)
[3] 劉軍生:植物新品種糾紛司法實踐中的若干問題,載《電子知識產權》2004年第10期
[4] 郝力、胡雪瑩:植物新品種侵權糾紛案件審理的問題,載《人民司法》2005年第1期
[5] 蔣志培、李劍、羅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載《知識產權審判指導》2006年第2輯
[6] 李劍:審理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件基本問題辨析,載《人民司法(應用)》2008年第7期
[7] 羅霞: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的相關思考,載《人民司法(應用)》2016年第7期
[8] 牟萍:植物品種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4-15頁
[9] 侯仰坤:論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
[10] 李劍:植物品種知識產權保護研究,中國人民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
[11] 臧寶清:植物新品種權名稱能否注冊為商標,載《中國知識產權報》2015 年11 月20 日第007 版
[12] 高景賀:植物新品種品種權名稱司法保護研究,載《河南科技》2017年第12期
[13] 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1978年文本第13條第2款、1991年文本第20條第2款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第27條
[15] 《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1978年文本第13條第8款、1991年文本第20條第8款
[16] 李菊丹: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67頁
[17] 張志偉、高景賀:論植物新品種名稱權的設定——品種權的二元屬性視角,載《中國發明與專利》2017年第11期
[18] 《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1978年文本第13條第2款、1991年文本第20條第2款。
[19] 侯仰坤:論植物新品種權名稱的特征和法律作用,載《知識產權》2015年第9期
[20] (2013)皖民三終字第00035號,合議庭:陶恒河、王玉圣、鄭霞,2013年6月26日。本案中,“冀優1號”是“冀玉10號”玉米新品種的生產試驗時的代號,徐春英銷售的玉米品種的外包裝上標注“冀優1號”,可以認定“冀優1號”和“冀玉10號”實為同一玉米品種
[21] (2009)鄭民三初字第440號,合議庭:趙磊、王富強、梁曉征,2009年9月26日。本案中,被告銷售人員出具品種為“中4號”的質量保證卡。
[22] (2010)一中民初字第11841號,合議庭:毛天鵬、李冰青、佟姝,2011年3月22日。本案中,“長玉19”系審定和授權谷子新品種,羅某某申請注冊“奧利長玉19”商標,并許可冠海公司經營包裝標有“奧利長玉19”文字的谷子產品,《種子銷售憑證》中“品種”欄顯示為“奧利長玉19(魯單203)”,《種子銷售代理合同》中“品種”欄顯示亦為“奧利長玉19(魯單203)
[23] 李瑞云、林祥明:關于農作物品種名稱的思考,載《中國種業》2009年第12期
[24] 劉鎮偉、余欣榮、張建龍:《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導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第93頁
[25](2009)豫法民三終字第04號、(2009)豫法民三終字第13號、(2009)豫法民三終字第17號、(2009)豫法民三終字第18號
[26] 王富強、馬靜:植物新品種假冒侵權行為分析,載《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22期。王富強:植物新品種名稱應受法律保護,載《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4期。李曉昱、王富強:植物新品種侵權判定熱點問題探析,載《中國審判》第2011年第4期。
[27](2019)最高法知民終14號,合議庭:周翔、羅霞、焦彥,2019年12月10日
[28] 周翔、羅霞、贠璇:植物新品種權保護范圍的確定,載《人民司法(應用)》2020年第1期
[29] 狄強、謝湘:關于植物新品種權保護條例中繁殖材料范圍界定的討論,載《科學導報·學術》2019 年第19期
[30] 李菊丹:“三紅蜜柚”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植物新品種司法保護的標桿案件,載《中國種業》2020年第1期
[3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裁判要旨(2019)》摘要,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5831.html,訪問日期2020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