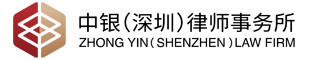相對于專利、商標和著作權業務,植物新品種案件屬于知識產權實務中相對“冷門”的板塊,植物新品種案件中涉及的專業性問題也未能獲得足夠的關注。司法案例中體現出的審判思路以及法院對爭議問題的闡明也沒有引起重視。作為在植物新品種司法保護耕耘十余年的專業律師,分析司法實務中的相關問題,既是因“事實與規范之間穿梭往返”的職業習慣的使然,也是因“促進育種創新、推動種業發展”的行業使命的召喚。本文基于植物新品種案件訴訟實務的邏輯,結合2007年品種權司法解釋出臺后的代表性案例,對值得關注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梳理,以期能見拋磚之效,助力植物新品種的司法保護。文章內容較多,分為系列文推送,本次推送為第三篇,主要涉及植物新品種權的權利內容。
四、植物新品種權的權利內容(訴什么)
根據《種子法》規定,完成育種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授權品種享有排他的獨占權,并考慮《條例》第33條規定的授權前的臨時保護,可以確定目前我國品種權的權利內容包括生產權、銷售權、使用權、許可權、轉讓權、名稱標記權[1] 以及追償權。上述權利內容并不包括UPOV公約91文本中的為繁殖而進行的種子處理、出口、進口以及以上述目的而進行的儲存。[2]品種權內容的明確對于植物新品種權的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非常重要[3],其不僅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誰有權提起侵權訴訟,而且還可能影響到植物新品種侵權與否的認定。
1、對品種申請權的侵犯
植物新品種侵權的前提是品種獲得授權,故因主張他人未經許可、就自己培育的品種提出植物新品種權申請而提起的訴訟不屬于侵權訴訟。在許某鳳、濟南永豐種業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種權權屬糾紛、植物新品種申請權權屬糾紛案中,[4]最高法院認為,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件中的侵權行為專指針對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在品種獲得授權前無法基于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提起侵權訴訟。認為他人未經許可、就自己培育的品種提出植物新品種權申請、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主張,屬于申請權歸屬和行使主體方面的爭議,本質上屬于行政法規規定的權屬糾紛,而非侵權糾紛。
2、生產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
在育種環節針對生產(繁殖)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最為典型。侵權人為規避法律責任往往使用代號指稱繁殖材料,此種情況下,多需要對被控侵權的繁殖材料是否為授權品種進行鑒定。在敦煌種業先鋒良種有限公司與張掖市奧林農業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石河子市金實種業有限責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5] 奧林公司委托金實公司繁育PS6玉米種子,金實公司實際種植623.5畝,經北京玉米種子檢測中心鑒定,PS6玉米種子實為“先玉335”玉米品種。最高法院認為,本案侵權種子的生產是由奧林公司提供親本、技術指導和金實公司提供土地、人力共同完成的,缺少其中任一公司的行為,侵權種子的大規模繁殖就無法完成,故奧林公司和金實公司構成共同侵權。生產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實際侵犯品種權人的生產權益。
需要說明的是:(1)這里的生產并不純粹指田間的種子生產,擴繁授權親本材料也是侵權;[6]雖如此,生產行為的認定并不需要以證明存在具體擴繁、嫁接等行為。被訴侵權的種植行為是否應當認定為生產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關鍵在于該植物體是否屬于繁殖材料,以及是否經過了品種權人許可。(2)單純的種植行為本身不屬于生產繁殖行為。在河北省高速公路京秦管理處、河北法潤林業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侵害“美人榆”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以下簡稱“美人榆”案件),[7] 雖然涉案美人榆為無性繁殖品種,其植株本身就是繁殖材料,但是,根據本案現有證據,以及法潤公司在庭審中關于“京秦管理處無擴繁行為”這一事實的認可,最高法院認為,在無證據顯示京秦管理處種植涉案美人榆苗木是為了銷售營利,且其并未實施扦插、嫁接等擴繁行為的情況下,種植行為本身既不屬于生產行為,也不屬于繁殖行為。
3、銷售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
在銷售環節以針對銷售(繁殖)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最具代表性。在壽光市綠鼎碩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先正達種苗(北京)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8] 最高法院認為,綠鼎碩公司未經許可為商業目的生產、銷售“索菲婭”繁殖材料的行為,經農業部植物新品種測試中心檢測,該索菲婭樣品與對照樣品奧黛麗比較位點數為22,差異位點數為0,即二者為同一品種,故綠鼎碩公司的涉案行為侵犯了先正達公司的“奧黛麗”植物新品種權。銷售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實際侵犯了品種權人的銷售權益。
需要說明的是:(1)這里的“銷售”,應結合我國加入的UPOV公約1978文本的相關規定理解,即“銷售”包括許諾銷售行為。在萊州市永恒國槐研究所與葛某軍侵害“雙季米槐”品種權侵權糾紛案中,[9] 最高法院認為,葛某軍通過合同磋商銷售“雙季米槐”繁殖材料的行為構成許諾銷售,屬于銷售行為的一種,故葛燕軍應當承擔停止侵害的民事責任。(2)因植物體的不同部分可能有著多種不同的使用用途,可作繁殖目的進行生產,也可用于直接消費或觀賞,同一植物材料有可能既是繁殖材料也是收獲材料。對于銷售者而言,應當審查銷售者銷售被訴侵權植物體的真實意圖,即其意圖是將該材料作為繁殖材料銷售還是作為收獲材料銷售。在前述“美人榆”案件中,最高法院認為,在無證據顯示京秦管理處種植涉案美人榆苗木是為了銷售營利,且其并未實施扦插、嫁接等擴繁行為的情況下,京秦管理處的相應種植行為亦不受品種權中銷售權能的調整。
4、重復使用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
對被控侵權人重復以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為親本與其他親本另行繁殖的,《司法解釋》將其認定為屬于以商業目的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在河南金博士種業股份有限公司訴北京德農種業有限公司、河南省農業科學院侵害玉米“鄭58”品種權侵權糾紛案中,[10] 最高法院認為,德農公司已經支付“鄭單958”品種權許可費2000萬元,并為生產“鄭單958”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因培育“鄭單958”必須使用親本“鄭58”,德農公司未經金博士公司同意,使用“鄭58”生產“鄭單958”,侵犯了金博士公司享有的“鄭58”植物新品種權。重復使用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實際侵犯品種權人的使用權益內容。
需要說明的是:(1)被控侵權人重復使用授權繁殖材料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并不必然侵犯另一品種的品種權。在安徽隆平高科種業有限公司訴甘肅金大地種業有限公司、盧加仁侵害玉米“L239”和“隆平206”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11]中,法院認為,雖然根據農業部相關標準和玉米品種鑒定DNA指紋方法,可以確定“隆平206”系親本之一“L239”的雜交種,但不能由此確定“隆平206”系“L239”的唯一子代;“隆平206”作為獨立玉米新品種在本案中尋求法律保護,缺乏與被控侵權玉米種子之間侵權聯系的相應證據。(2)植物新品種侵權行為是指生產行為、銷售行為,不包括使用行為。對于使用者抗辯其屬于使用行為而非生產行為,應當審查使用者的實際使用行為,即是將該收獲材料直接用于消費還是將其用于繁殖授權品種。在安徽隆平高科種業有限公司訴田某軍侵害玉米“L239”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12] 法院認為,雖然田某軍具有農民身份,但根據證據保全程序中確定的被控侵權品種的種植畝數,以及考慮玉米制種比一般種植成本高、產量低的特點,認定其構成品種權侵權。(3)單純的種植行為不屬于種子法上規定的“將授權品種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繁殖材料”的行為。在前述“美人榆”案件中,最高法院認為,在無證據顯示京秦管理處種植涉案美人榆苗木是為了銷售營利,且其并未實施扦插、嫁接等擴繁行為的情況下,單純的種植行為也不屬于種子法上規定的“將授權品種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繁殖材料”的行為,故京秦管理處的被訴侵權行為并未侵害河北省林業科學研究院、法潤公司享有的“美人榆”品種權。
5、對限定區域的被許可人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
品種權人既可以自行實施生產、銷售授權繁殖材料,也許可他人實施品種權。許可類型可以是獨占許可、排他許可、普通許可。實務中對于能否基于限定區域的實施許可而單獨提起訴訟存有爭議。在陜西省涇陽縣現代種業有限責任公司與楊凌新西北種業有限公司侵害“豫麥49-198”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13] 法院認為,因平安公司對豐源公司的授權限于溫縣區域,現代公司明知豐源公司無權授權其在陜西區域內經營豫麥49-198品種,平安公司亦向陜西工商部門明確表示新西北公司是其在陜西境內授權的唯一一家生產、加工、銷售豫麥49-198品種的單位,故現代公司關于新西北公司不是本案適格原告的主張不能成立。在安徽皖墾種業股份有限公司、壽縣向東汽車電器修理部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14] 最高法院認為,對于限定特定地域范圍的獨占實施許可而言,由于地域范圍的劃分而使品種權行使主體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并不屬于真正的獨占實施許可。但是由于皖墾種業公司取得了品種權人的明確授權,符合司法解釋有關普通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提起訴訟所規定的條件,有權提起本案訴訟。對限定區域的被許可人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實際侵犯品種權人的許可權益。
6、受讓人生產銷售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
品種權人既可以許可他人實施,也可以轉讓給他人實施品種權。但品種權轉讓,未進行登記公示之前,品種權轉讓行為不生效。在甘肅省敦煌種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河南宏展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吉祥1號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最高法院認為,植物新品種權的著錄事項變更登記雖然是一種行政管理措施,但其涉及權利人利益的同時,也涉及公眾的利益,其變動應當進行公示,植物新品種的權利變動向行政機關進行登記公示才具有權利外觀。因此,品種權沒有進行登記公示之前,品種權轉讓行為并未生效,故不能認定武威農科院是“吉祥1號”唯一的品種權人。[15] 受讓人生產銷售授權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實際侵犯品種權人的轉讓權益。
7、假冒授權品種對名稱標記權的侵犯
《條例》第40條和《種子法》第73條第6款均規定,假冒授權品種的,可以責令停止假冒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和植物品種繁殖材料。但依據規定內容無法判斷假冒授權品種是否屬于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的行為,該問題爭議已久。有觀點認為,假冒授權品種行為屬于欺詐行為甚或生產銷售假劣種子的行為,不屬于侵犯品種權。[16] 其它觀點認為假冒品種在市場上銷售,必然有損品種權人的聲譽,進而損害品種權人通過生產、銷售授權品種獲益的權利。[17] 假冒授權品種直接侵犯品種權人的名稱標記權益,應屬于廣義侵權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有直接將銷售假冒授權品種認定侵權行為的做法。在北京聯創種業有限公司與王保敏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18] 法院認為,任何人未經品種權人的許可,為生產經營目的生產或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銷售假冒授權品種的種子,即侵犯了品種權人的權益,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江蘇明天種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遠縣山泉農資經營部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19]中,法院認為,侵犯植物新品種權和假冒授權品種同樣屬于侵權行為、違法行為,二者既受《種子法》調整,亦屬于《侵權責任法》、《民法通則》等法律調整的范疇。
需要說明的是實際權利人關于品種權名稱及育種者名稱的恢復的權利。在利馬格蘭歐洲、黑龍江陽光種業有限公司等與甘肅恒基種業有限責任公司追償權糾紛案中,[20] 法院認為,利馬格蘭歐洲作為"利合228"玉米品種權人,向國家級或省級農業部門申請審定該品種時,必須使用"利合228"名稱;由于"利合228"與"哈育189"是同一玉米品種,"哈育189"已通過黑龍江省的品種審定,因此,在該審定未經更正或撤銷的情況下,利馬格蘭歐洲不能通過"利合228"品種審定,也無法在黑龍江省適宜區域推廣、生產、銷售"利合228"玉米品種。同時,陽光種業公司與黑龍江農科院玉米研究所也不能再進行"哈育189"品種的生產與銷售等行為,否則,屬于侵權行為。造成這種結果,均因陽光種業公司與黑龍江農科院玉米研究所在申報審定品種時填報品種名稱和育種者名稱不真實、不符合法律規定所致,該行為已對利馬格蘭歐洲造成損害,其應承擔停止侵權的法律責任,故利馬格蘭歐洲要求其將審定品種"哈育189"名稱變更為"利合228"、將"哈育189"審定公告中的育種單位由陽光種業公司與黑龍江農科院玉米研究所變更為利馬格蘭歐洲的訴請應當予以支持。
8、對授權前生產銷售繁殖材料侵權行為的追償
《條例》第33條規定,品種權人可以對初審公告之日起至授權之日期間的為商業目的生產銷售繁殖材料的行為進行追償。其立法目的在于給予授權品種臨時保護期,全面保護品種權人的科技成果。在上訴利馬格蘭歐洲、黑龍江陽光種業有限公司等與甘肅恒基種業有限責任公司追償權糾紛案[21]中,法院認為,依據民法權利法定原則,利馬格蘭歐洲經我國農業部依法授權取得了"利合228"玉米新品種權,其有權行使追償權。根據本案查明事實,未經利馬格蘭歐洲許可,陽光種業公司在追償期內為商業經營目的以"哈育189"的名義生產、銷售"利合228"玉米新品種權的種子,利馬格蘭歐洲依法應該得到相應的經濟補償。授權前的生產銷售繁殖材料的侵權行為,實際侵犯品種權人授權前的臨時性追償權。
注釋:
[1] 李劍:植物品種知識產權保護研究,中國人民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
[2] 牟萍:植物品種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第175-176頁
[3] 牟萍:植物品種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第181頁
[4](2019)最高法知民轄終308、309號,合議庭:岑宏宇、陳瑞子、何鵬,2019年9月24日
[5](2014)民提字第31號民事判決,合議庭:李劍、宋淑華、吳蓉,2014年12月19日
[6] 劉振偉余欣榮張建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導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96頁
[7](2018)最高法民再290號,合議庭:朱理、毛立華、佟姝,2018年12月29日
[8](2019)最高法知民終703號,合議庭:劉曉軍、唐小妹、李自柱,2020年2月3日
[9](2017)最高法民申4999號民事裁定,合議庭:朱理、毛立華、佟姝,2017年12月26日
[10](2018)最高法民申4587號,合議庭:王闖、朱理、毛立華,2019年1月31日
[11](2016)甘民終78號,合議庭:李紅、李雪亮、劉錦輝,2016年2月25日
[12](2015)甘民三終字第5號,合議庭:李紅、李雪亮、劉錦輝,2015年3月20日
[13](2009)陜民三終字第42號,合議庭:趙欣同、惠會、馮炬,2009年11月11日
[14](2019)最高法民再371號,合議庭:秦元明、周波、馬秀榮、張晨祎,2019年12月25日
[15](2014)民申字第53號,合議庭:周翔、羅霞、周云川,2014年5月21日
[16] 武合講:假冒授權品種不侵犯品種權,載《種子世界》2014年第1期
[17] 李劍: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基本問題辨析,載《知識產權審判指導》2008年第1輯
[18](2019)皖01民初1055號,合議庭:張麗紅、胡娟、許琛、丁延奇,2019年7月23日
[19](2018)皖民終8號,合議庭:張蘇沁、徐旭紅、馬士鵬,2018年6月11日
[20](2018)甘民終695號,合議庭:劉恒、劉錦輝、宋巍,2018年11月28日
[21](2018)甘民終695號,合議庭:劉恒、劉錦輝、宋巍,2018年11月28日